你真的看懂《爆裂无声》了吗?
你真的看懂《爆裂无声》了吗?
保民是个哑巴,他不能说话,但是他是一个能听到声音的西北男人。他不是天生的哑巴,以前和别人打架把自己舌头咬断了,一件破破烂烂的绿棉袄,黝黑的皮肤上布满络腮胡茬。保民的妻子因为矿业老板非法开采,导致水污染,身患慢性病,村长知道水污染严重,所以家里面所有的生活用水都买的瓶装矿泉水。

当地的黑心煤老板昌万年,喜欢涮火锅,羊肉在桌面上摆了几十盘,昌万年仗着自己有钱,有人,有律师,在当地称霸一方,有一天保民的儿子去放羊,羊渴了在喝水,可是保民的儿子失踪了,这个事是昌万年干的,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事被羊肉馆老板的儿子发现了,孩子亲眼目睹了昌万年和律师怎么加害保民的儿子的过程。
羊肉馆老板因为村子的事情,在村长怂恿下和保民斗起口角,打架过程中保民误伤了羊肉馆老板的眼睛,成了独眼龙,可是保民后来在解救律师女儿的过程中,羊肉馆老板还救了他。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这是讲的那个故事,这是电影《爆裂无声》的部分故事情节,属于一部西部的故事片,能看懂的要刷好几遍,看不懂的,觉得很普通。
《暴裂无声》的拍摄地是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在塞外的广阔草原上生长的中国人平素更擅食牛羊,而非像黄河以南的同胞那样嗜猪为命,忻钰坤无疑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地域特征,赋予了它别样的寓意。羊在中国千年的文化迭代中被赋予了“懦弱、善良与被奴役”的刻板印象,古时每逢灾年甚至还会把人称为“两脚羊”以供屠戮充饥。在影片中,羊的能指对应的是社会底层,或是贫下中农的所指,甚至角色不同的吃羊方式也同样暗含了背后阶级的差异。

在影片中,无论是姜武饰演的煤老板昌万年,还是张保民同村的村民都有相对应的吃羊桥段,这也牵引出了两场最为重要的饭桌戏码。第一场食羊戏源自张保民初回老家,到羊肉馆仇人家打听儿子近况。导演先是给了几个主观镜头交代了张保民凝视着围坐在火锅前大口吮吸羊蝎子的村民,之后运用了心理蒙太奇的手法拓展了影片的叙事时空,同时阐述了张保民因不愿伙同贪婪地村民将土地出卖给煤矿,再次给张保民这个角色加深了野蛮与执拗的脾性的性格烙印。除此之外,导演也用“食羊”隐喻了村民与煤矿公司的同流合污。在闪回的饭局戏中,本在吃羊蝎子的张保民一听到“签合同”便放下了手中的羊肉,与前来劝阻他的屠夫大打出手,也预示着张保民将会是这个黑暗社会下唯一的逆行者。

第二场食羊戏同样服务于主要人物形象与阶级观的塑造,这场忻钰坤聚焦于昌万年的呈现,它将毫无生气地自动切肉机置于后景,将盛满羊肉片的十几张盘子置于前景,而昌万年则稳居其中。前者预示昌万年本人为了牟取利益不惜一切代价的冰冷手段,后者诉说着他的掌控欲,明明只有一人吃,却让羊肉摆满了一整桌。这场用冷峻镜语拍出的饭桌戏似乎也为紧接着他折磨竞争对手的戏码作了预叙,表明了他在影片中绝对的上层地位。
金字塔形象同样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能指符号,它分别指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阶级观”与“张磊的命运”。影片一开始张保民的孩子张磊在电塔下摆放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石碓,与他名字中的“磊”相契合。当叙事角度回到张保民视角时,导演特意给予了金字塔石碓一个主观镜头,此时的石碓已经崩塌,预叙了张磊已经死亡的事实,为张保民的行为增添了一丝西西弗般的无力感。金字塔形象再次出现时,影片的视角转为了昌万年的视点,一个金字塔的摆件就放在他的供桌上,其顶层被镶上了金边,昭示着他的绝对权威。

同样,如果我们把暴发户昌万年的艺术形象指向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杂合体时,律师徐文杰因其人性两面性被归类为了带有两重性的中产阶级群体上,张保民和其妻儿则自然而然地背负上了贫下中农的身份隐喻。以张保民为首的贫下中农形象在影片中是十分值得玩味的,在解放前左翼电影与战后电影时期,底层人虽然常常表现为经历各方压迫的悲苦形象,但由于创作者自身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其结局往往是合乎好莱坞式的温情与影戏观制衡下的善必胜恶主题的。当时间迈入十七年时期,以《白毛女》《祝福》《我这一辈子》为首的展现阶级矛盾的电影中,底层人第一次得到了觉醒,他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弃子,也非是导演呈现对美好未来的剧作木偶,而是被赋予了阶级觉悟与革命观的新人。他们的结局往往脱离了影戏观电影下突兀地圆满,而是因新时代的来临让鬼变成了人,让穷人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忻钰坤在影片中所要展现的底层形象必然要脱离了以往高度概括化、典型化的窠臼,向着更加立体的、有着性格多重侧面,甚至是弱点的普通身份的人出发。张保民就被忻钰坤赋予了“哑巴”这一特点,这既是符合情节逻辑的人物特征,又是极其具有隐喻色彩的符号。他的哑正巧代表着底层人在当下社会下话语权的缺失,他不愿也没能力为自己的权利讲话。在一般的商业电影中,如果主人公失去了某种感官器官,他肯定会被编剧赋予其他方面的特长。然而在《暴裂无声》中,张保民并没有因聋哑获得超于常人的判断力、思维能力,甚至他的形象相较于其他人来说是一种退步。
导演用各种象征性镜头向观众暗示了张磊的死是由徐文杰和昌万年一手造成的,然而在影片内的张保民却次次被身居高位者的一席话语欺骗、利用,甚至直至影片最后若不是剧作扣子被解开,他可能一辈子无法得知自己孩子的命运。导演给张保民的那种超乎常人的搏击能力,如今想来应该更多出于市场需求的考虑,用拳拳到肉大众兴趣为主导的叙事创作淡化了人物的悲苦宿命。
《暴裂无声》中不断出现的隐喻和象征符号无疑深化了影片的时空深度,为以情节剧为框架的视听语言和叙事创作上增添了一丝现实主义的观照。使影片有别于具有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强调创作的《钢的琴》等影片,但忻钰坤对于符号的使用仍没有达到流畅的水准,大有堆砌之嫌,影片中没有使用方言和非职业演员也大大削弱了底层苦涩生活原生态的无奈与无可把握。
-

- 我军中的著名战斗英雄,您了解几个?
-
2025-02-17 16:44:27
-

- 范晓萱20岁红遍大江南北,再到被贴上坏女孩的标签
-
2025-02-17 16:42:10
-

- 银川十大旅游胜地!来宁夏旅游不可不去的几个景点
-
2025-02-17 16:39:55
-

- 兰州一中贾立平 参加最强大脑被誉为魔方王子
-
2025-02-17 16:37:39
-

- 刘德华与喻可欣的故事:不仅公开谈房中私事,还把恋爱过程出书!
-
2025-02-16 13:17:45
-

- 宽容是什么
-
2025-02-16 13:15:29
-

- 细数中国顶级酒店(上海 上篇)
-
2025-02-16 13:13:13
-

- 笼罩满清兴衰史的叶赫那拉诅咒有多可怕,歌坛一姐原名叶赫那拉英
-
2025-02-16 13:10:58
-

- 今夏被“米杏色”惊艳了!不仅衬肤显白、还优雅高级,谁穿谁好看
-
2025-02-16 13:08:41
-

- 深度揭秘杨超越背后公司-传递娱乐,到底有多牛?
-
2025-02-16 13:06:25
-

- 埃及胡子鲶40年的“野心”:折腾完珠江,又北上黄河,能得逞?
-
2025-02-16 13:04:10
-

- 4300张复仇者联盟原画图集,每一个都值得收藏!网友:非常想要
-
2025-02-16 13:01:5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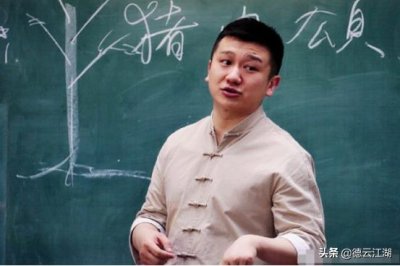
- 大逗相声学费9880元,德云社学费2万元,曲艺界人才竞争太激烈
-
2025-02-16 12:59:37
-

- 《金粉世家》结局凄惨,我们为什么意难平?这四个真相说明一切
-
2025-02-16 12:57:22
-

- “苦命原配”马伊琍的坎坷情史
-
2025-02-15 21:15:43
-

- 知天命是多少岁 古代年龄的解析
-
2025-02-15 21:13:27
-

- 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煮茶品茗如人生:一选,二等,三精
-
2025-02-15 21:11:10
-

- 辽宁省营口市十大景点是哪些?自驾游玩如何安排行程?
-
2025-02-15 21:08:55
-

- 12部韩国顶级黑帮电影!节奏稳而紧,题材和尺度开放!你看过几部?
-
2025-02-15 21:06:39
-

- 周莹:慈禧的“干女儿”,晚清陕西女首富,生前荣华死后尸骨难存
-
2025-02-15 21:04:23



 一个鸡蛋就可以让绿萝疯长
一个鸡蛋就可以让绿萝疯长 酒店偷拍黑产调查:酒店偷拍直播“不愁卖”,万部视频付费看
酒店偷拍黑产调查:酒店偷拍直播“不愁卖”,万部视频付费看